增长的限制–第二部分
增长的限制–第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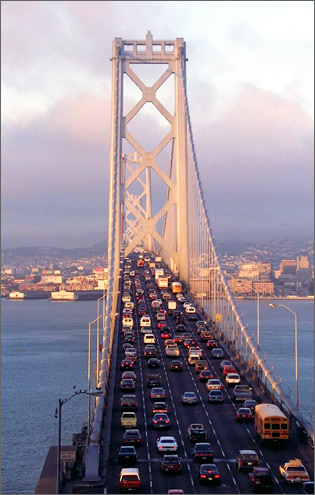
香港:如何保证在不耗尽全球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发展全球经济并保持其可持续发展?这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的问题。此次金融危机向人类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警醒:正是因为没有努力争取可持续发展,这才导致全球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气候改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活动和无节制的过度开发,而这给人类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仅仅在五年前,许多政府、官员和公司还否认并拒绝对非持续发展方式采取限制措施。如今,金融界所依赖的市场机制正遭受严重的破坏,甚至对自然界也造成了影响。
金融危机的起因——次级抵押贷款——告诉我们非持续发展方式的后果有多么严重。那些在美国获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人其实并非都是穷困潦倒和无家可归的人。根据 责任贷款中心(the Center for Responsible Lending)的数据显示,那些在1998至2006年间获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人中,有90%的人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同时,就生活和住房质量而 言,他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前10%。同时,对住房的再融资又进一步刺激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又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去购买 第二套房子和其他奢侈品。凭借银行能够提供超额的资金贷款,很多人的消费能力其实早已大大超出了他们实际的支付能力。而建这样的第二套住房所耗费的建材不 仅耗去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住房的供热和制冷设备又进一步消耗了大量能源。
显然,消费者并不是唯一的破坏者。在巨额收入回报的诱惑下,银行培养了一种“越多越大就是越好”的文化,忽视了如此高风险贷款将会引发的贷款回收问题。银 行贷款给那些没有资格、不符合条件的借贷者,最终导致了房地产价格暴跌、美国经济放缓、银行资产数以万亿的蒸发,并导致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积蓄化为乌有。
随着气候的改变,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并行的轨迹:人们乐观地面对自然灾害,就如同很多乐观者坚信市场最终能够扭转败局。现在,这种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又 一次为伦敦和纽约的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中心所推动。许多决策者都把希望寄托在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上,即用消耗碳的信用额度或将其赌注置放在可再生项目的投资 上,以此解决环境危机。
然而事实上,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而且它们的潜力所能制造的问题要远远多于它们所能够提供的解决办法。
只要仔细考察一下碳交易,就能在这些猖獗的问题背后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首先,由于允许从其他地区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指标,鼓励了这一行为的猖獗,而这使得碳交易不但没有减少废弃排放,而且还不必承担排放污染物的责任。
正如信用评级工具是不可信的一样,碳交易同样是不可靠的。贸易公司不赞同通过简单的抵消计算得出信用水平,而是更倾向于通过投资廉价和短期项目取得信用水平的“快速定位”。
救济措施要求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仍是贫困潦倒的,即使是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也有几乎半数的人口仍在为每天挣得2美元或 更少的钱而斗争。即使导致本国政治处于险境,也没有哪个政府(无论是民主的政府还是非民主的政府)会采用西方银行所运作的复杂的全球贸易计划和冒险损害自 己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
可再生能源计划也同样容易被滥用。随着风险愈来愈高和投资者愈加贪婪,银行家和律师们也将制定出越发复杂和越发不透明的金融工具,以将其触角伸进潜在的发 展之中——这在排放量交易市场中已经出现。其结果是,不考虑严重后果只注重短期利益的交易越来越多。如此一来,他们的关注重点无疑会从如何缓解危机被扭曲 到如何获取利润增殖上去。在危机爆发之前,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是不可能为竞争性市场所自我修正的。
过分依靠市场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引发的问题已经显而易见。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迅速减少,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以及银行家们做出的决策。事 实上,这些银行家们并不懂得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重要意义,他们只是在短期利润驱使下做出上述决策的。《新能源金融》指出,2008年第三季度对清洁能源的风 险资本和私人股本投资较上季度相比下降了24%。这对中国等国家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因为中国计划到202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而这需要2万亿元 人民币即约合2900亿美元的投资。即使是在衰退中但却仍然保持强劲发展态势的领域,即在清洁能源技术和构建新增效益如风力发电或太阳能公园等的早期阶段 的风险投资中,工程项目的投资者所倚仗的仍然是那些因固守利润最大化而分崩离析的华尔街机构。
在消费驱动的疯狂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大自然对它的制约。但是,因不当动机和过度消费而遭到破坏的市场,却已经忽视了这种预警信号。甚至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 格林斯潘,一位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奉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支持不受管制之自由市场的做法“在部分上”是错误的。他承认自己错误地以为,银行即使完全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也会保护股东及其在其机构中的资产。赞同市场幻灭说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认为,“原生资本主义已经死亡。”
发展“无限制”的态度是不切实际的。颇有希望的是,那种对市场机制的坚定信念正开始失去其可信性。
随着全球市场的震荡,政府已经介入——而气候问题也该如此处理。全球公共利益不应该被置于无节制的金融家们私人利益的祭坛上。就气候变化而言,清洁技术项目需要资金,这些资金应该来自国库,而不应通过那些旨在为少数控制资金流的人创造巨额利润的金融工具。
必须找到更好的策略去应对气候变化。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事情:减少排放量要求迅速削减对矿物燃料的消费,而这意味着要对那种以促进无节制消费为基础的发展进行限制。
那些对限制措施持有疑义者,只需看一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2008年生命星球报告》中的统计数据:人类每年使用的自然资源要超过地球自身每 年可再生资源的30%。因此,该报告的作者指出,每年的生态债务高达4.5万亿美元。(该数字是根据一份联合国报告中对每年通过破坏生态环境所获得的经济 价值予以估价得出的。计算包含了因农作物所需降水量减少、防汛减弱、土地侵蚀、碳汇丧失和生物多样性等的经济影响。)
对那些不限制生态消费模式的国家所做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所追求的经济增长,也引发了促使金融危机发生的过度消费。三个生态债务国的人口和 消费模式显著地表明:美国消耗的资源是其国家生物承载力或者说资源生产和排放吸收可用面积的1.8倍;中国和印度分别是2.3倍和2.2倍。人均可用生物 承载力是2.1公顷,而实际人均使用面积高达2.7公顷。美国人平均需要9.4公顷。
在有关减少排放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引入之前,保护人类所需要的真正创新措施是不可能出现的。要严格实行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关键,乃在于少数人要能够完全地 为更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但是,意识和诚恳的措辞并不等于行动。当然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专制政体比所谓的自由民主政体更易于执 行。例如,为了降低北京的污染程度,中国就曾设法通过对一个星期中的某几天限制汽车出行来减少废气排放。公众接受这一保护更大公共利益的政策表明:有效地 解决气候危机的方式取决于采取不受既得利益集团政治干预之影响的行动。
金融危机证明了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保护公众利益。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健全的法规也同样不可或缺。决策者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已经遭到了来自气候变化的报应,因此决策者也不应该再受市场权宜之计的诱惑。
钱德兰•纳伊尔是全球未来研究所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